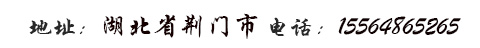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4逃离硅谷逃离
|
北京医院治疗皮肤病 http://pf.39.net/bdfyy/bdfjc/210403/8810613.html 本文主要探讨高成本对硅谷及深圳创新产业的影响问题。 因此需要先定义硅谷地区的范围及面积。深圳不需要定义,其行政辖区面积为.5平方公里。 硅谷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定义,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地方政府管理。根据硅谷指数的定义,早期硅谷只包括圣塔克拉拉县的部分区域。后来,硅谷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年开始,硅谷指数已把整个圣马特奥县包括进去,之后因为旧金山市区的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所以旧金山也被纳入硅谷指数的统计范围。现在,广义的硅谷还可以包含整个旧金山大湾区,湾区面积平方公里,人口万。 狭义的硅谷即旧金山以南、圣克鲁斯以北的狭长地带,面积约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深圳市加上莞、惠临深地带平方公里。硅谷的核心地带主要是圣克拉拉县与圣马特奥县的主要都会区域,面积约平方公里,也与深圳都市核心区平方公里相当。 从地理范围规模来说,二者具有一定可比性。 一 我们可以恬不知耻地说,深圳与硅谷都饱受高成本导致的资源流出困扰,其中核心要素成本的高昂,主要是高房价。 硅谷房价在21世纪头10年曾经有过两次下跌。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年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只剩下高峰时期的1/3。在此后的年金融危机中,被炒高的硅谷住房泡沫也破灭了,硅谷房价中位数下降了30%,有些地方甚至下降了50%。但年之后,硅谷房价就一直处于升势之中。 从年至年初,硅谷住房销售套均价由67万美元一路升至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7.3%。同一时期,金融中心纽约的套均价由46万美元上升至57万美元,年复合增长仅2%。而全美平均房价,迄今仅29万美元一套,十年几乎零增长。 根据科威国际不动产(ColdwellBanker)的一份房屋价格报告,全美买房最贵的10个城市都在加州,其中7个城市在旧金山湾区,其余的都在南加州。 年上半年,旧金山市的房价创下历史最高半年涨幅。当年7月,市区平均房价为万美元,半年内涨了20万美元。平均一套公寓为万美元。平均房租从年的每月美元,上涨到年的美元。旧金山超过了纽约曼哈顿,成为美国最为昂贵的都市区。湾区的房价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而旧金山更是全美平均水平的8倍。 年11月,美国房地产公司ColdwellBanker公布其年度房屋上市报告(HomeListingReport),报告中将全美2个房产市场上的四室两卫户型平均标价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湾区帕洛阿图(PaloAlto)这一户型的平均价格高达万美元列为全美第二高价,排名第一的是橙县(OrangeCounty)的NewportBeach,平均价格是万美元。 房价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住房可负担能力问题。 根据加州房产经纪协会年8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旧金山湾区只有18%的人能够负担一间中位数价格的居住成本。根据年的数据,湾区人均年收入约为10万美元。 Edelman公司年调查发现,加州居民有71%的可支配收入用在了还房贷或者租房中,硅谷的住房成本占收入比高达77%。 若按照收入水平把硅谷的人群分为三部分,则低收入群体占比约为38%,中等收入群体约占36%,高收入群体占26%。其中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分界线为12.3万美元,中等收入与低收入的分界线为5.1万美元。 事实上,湾区90%的人没有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工作,75%的人不具备高学历。 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达舍说:"当一个地方的房价对人工智能工程师而言不成问题,而对诸如老师、警察、普通公司的普通员工而言成问题的时候,这就是大问题了。" 正是由于生活成本高企,最近几年里不断有科技公司迁出硅谷的报道。 根据CrunchBase的报告:就在年上半年,已经有许多初创企业、甚至是规模大的企业搬离硅谷,迁往Texas,比如美国前十大公司特斯拉,公开表示将总部立即迁往Texas/Nevada;知名企业QuestionPro更是早在1月就将其全球总部从旧金山迁至奥斯汀;紧接着4月,另一家名为Airtable的初创公司,也在奥斯汀开了一家办公室... 慧与公司(HewlettPackardEnterprise)计划将其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迁至休斯顿。该公司表示,其已经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建造了一个"最先进"的新园区。慧与还公布了超出分析师预期的季度营收,表明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正在升级数据中心的硬件。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Co.)于年拆分成立了慧与。 年10月,《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离开硅谷。 该报道称,年,离开旧金山的美国人比到那里的要多。根据最近一项调查,46%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湾区,高于年的34%。如此多的初创企业正在向新的地区拓展,以至于这一趋势有了一个名称--"离开硅谷潮"。堪称硅谷最受瞩目的风险资本家的彼得·蒂尔就是其中之一。年,硅谷投资人将一半资金投向了湾区以外的初创企业;如今,这一数字接近2/3。 "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硅谷开销巨大。生活成本在全球名列前茅。一位公司创始人估算,年轻的初创企业在湾区的运营费用至少高出美国其他城市四倍。从量子计算到合成生物学的新技术的利润率低于互联网服务业,这使得对于这些新兴领域的初创企业来说,节省资金更为重要。" 该报道甚至提到了深圳:"其他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也在上升。追踪创业精神的非营利组织考夫曼基金会基于初创企业和新企业家的密度,现在将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地区列为美国初创企业活动的第一名。蒂尔正在搬往洛杉矶,那里有着充满活力的科技景象。菲尼克斯和匹兹堡已经成为自动驾驶汽车中心;纽约成为媒体初创企业中心;伦敦成为金融科技中心;深圳成为硬件中心。所有这些地方仅靠自身都无法与硅谷匹敌;它们指向的是一个创新更分散的世界。" 也许我应该将深圳房价与硅谷作一个对比。但我之前在"柏拉图洞穴会所"发表的四篇长达9万多字关于深圳房地产问题的文章(金心异:深圳房地产问题之第三方批判),已将深圳高房价问题作了全面的展现和分析,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只就一个关键性指标进行对比:房价收入比。按照硅谷地区房价中位数为万美元,而收入的中位数为10万美元,则其房价收入比也不过是12。而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则早就突破了40. 年,深圳人均月收入在元人民币(全年7.2万,接近1万美元)以下的就业人口占比为62.5%,月薪1万元以上(年收入12万,接近2万美元)的占比仅为11.2%。全部就业人口的平均月薪则仅为元人民币,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 而深圳的住宅均价已达到8.8万每平米,一套平米的房屋需要万人民币,接近硅谷万美元的水平。即便是50平米的房屋,也要接近60万美元。但是硅谷万美元中位价的,可是独立屋而不是公寓啊。 《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渴望成为中国的硅谷。然而,尽管深圳拥有数家著名科技公司,但是深圳只在一个不怎么让人感到羡慕的地方跟硅谷最相似--高昂的房价。" 深圳的产业空心化程度,则要比硅谷严重得多。对此我也有多篇文章进行过论述,为了避免被贴上"深黑"的标签而被"严厉打击",我这里也就不再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我的旧文。说科技制造业过去五六年里在逃离深圳,也并不为过。 事实是,硅谷的科技公司可以逃向南加州、得克萨斯、北卡三角区,而深圳的科技公司则可以迁往上海、武汉、长沙、成都、郑州等地。 二 但是,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深圳,都有完全不同的声音:高房价不影响其吸引力! 中国某财经杂志报道逃离硅谷潮时,用了一个标题:"一千个逃离硅谷的理由,和一个留下的原因":高昂的房租,封闭的社区,巨头的垄断,硅谷的人才正在流失,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 美国求职网站Indeed显示,有35%的工程师在寻找硅谷以外的工作机会,依然有66%的工程师想进来。 吴军则在《硅谷之谜》一书中认为,"高成本导致了正向淘汰。" "硅谷地区和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不同,还在于并非哪个公司在那里站住脚之后,就能够一辈子呆下去,这也是硅谷地区与世界其他工业中心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在很多传统的工业中心,通常是最早进驻那里的公司占据着最好的位置,新的公司只能到周边稍偏僻一点的地区去发展。但是随着产业的变迁,占据最好位置的公司,往往不再是发展最快的公司了,从合理利用资源的角度来讲,它们应该让出来,但通常又赖着不走,直到把那个地区搞萧条了为止。但是硅谷地区不是这样做的。它靠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随着硅谷生活成本和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只有少数利润足够高、发展足够快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就得搬离硅谷地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硅谷完成了几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会淘汰掉一批公司,同时带来新的、更挣钱的商业机会。" "在硅谷每一次的产业变迁过程中,难免有很多人会失业,其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工作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从此在硅谷找不到工作,最终不得不搬出硅谷地区。对这些人来讲,这似乎有些残忍…但这样一来,经过很多年的发展,硅谷在整个IT行业的水平和地位才会不断提升。最终发展的结果是,只有不断追求卓越的人和伟大的公司,才能在硅谷地区立住脚。" 哈工大(深圳)经济学教授唐杰也认为深圳与硅谷高房价很正常:"房价和经济密度、人口密度有关。比如说,旧金山地区过去十多年一直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城市,在分析原因时,除去经济繁荣活跃外,一般看法是,旧金山地区土地面积紧缺,住宅用地供给明显不足是引起房价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深圳的房价为什么高?同样,深圳的区域面积是平方公里,人口是万,深圳房价高是因为它的经济活动密度高、人口密度太高。我们算过一笔账,假如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面积按照平方公里来计算,几个城市的房价会和深圳一样高,差价来自于京沪穗的城市面积大。" 总的来说,一致的看法是,深圳和硅谷的房价高,有它高的道理:房价高,说明想在这里买房的有钱人多,供不应求,说明这里经济发展质量高,单位面积创造的财富多,而且房价高才有排挤效应,排挤落后产业和产能,能留下来的都是高质量的优质产业…大概如此。对此,我在《深圳房地产问题第三方批判》长文中也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反驳,这里也不再重复。 三 辨析深圳与硅谷房价谁高谁低、是否合理,不是本文的主旨。我想要探讨的是:高房价、高成本会否对科技创新、对科技产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那么在企业的综合要素成本中,包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土地成本等。高房价主要影响到的是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 对硅谷来说,土地成本由于其稀缺性而大幅提高,其结果是办公室、厂房和住宅价格都会提高,并进而抬高劳动力成本。 对于中国大陆包括深圳在内的大部分城市来说,过去20多年一直采取的是如下的策略组合:保障工业用地供给、采用各种手段压低工业(产业)用地价格,同时减少住宅用地供给以拉抬住宅用地价格,以卖宅地收入补贴财政,以财政补贴科技工业。 因此对深圳的科技企业来说,如果是地方政府想要力保的产业,则其产业用地价格会是相对比较低的,土地成本在其要素成本中并不特别高。对中小科技企业来说,它们在深圳生存发展的瓶颈是根本得不到产业用地,而不是产业用地成本太高。 但目前对深圳构成最大冲击的,是劳动力成本。特别是科技公司的研发人才、工程师。年的数据,深圳共有研发人员18万人。深圳当然是希望不断扩大这个数目,而不是不断减少。但是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就将其近5万研发人员从深圳迁往东莞。 无论是研发人员、工程师逃离深圳,还是深圳对研发人员的吸引力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房价为核心的生活成本过高。深圳的工程师、研发人员供给,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中西部地区的理工科大学,诸如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但现在武汉、成都、西安等,以及长沙、郑州等,科技产业尤其是ICT产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城市房价远低于深圳,因而对工程师的吸引力远大于深圳,过去10多年间已有明确的发展态势表明,它们截留了相当多的研发人才,深圳的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等,也都在这些城市设立机构和平台,就地利用其研发人才(所谓"坑口电厂")。 一方面,深圳的平均薪酬水平,已不复年代的绝对领先全国,现在更落后于京沪等城市,另一方面,深圳的房价却超过京沪(京沪虽然其CBD地带房价也藤贵,但整个市域范围内仍有大量低成本居住区),这使得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深圳对研发人员、工程师人才的吸引力大幅下降,难免会影响到深圳的创新力。尤其是,深圳需要的是来自中西部地区能够吃苦耐劳的小镇青年,而不是家境优渥、不肯加班的海归博士。 硅谷与深圳皆不是以源头创新(所谓从0到1的创新)为主要方向。如果说硅谷擅长的是将技术创新迅速做出最好的产品、占领最大的市场的话,那么深圳在全球价值链里面,占据的是较硅谷还要低许多的位置。 深圳的科技产业创新,主要是硬件的创新(大部分属于10到的环节,甚至可以说是50-60的创新),与硅谷早已转向软件产业的创新尚有较大差距。虽然也有少量企业如华为、腾讯等转向了软件领域的创新,但整体上,深圳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仍然是由硬件制造能力奠定的。 而硬件制造,相对来说更加对成本敏感。所以深圳对高成本的承受力,可以肯定要远逊于硅谷。但深圳的生活成本,却又远高于硅谷(深圳40-45的房价收入比,相对于硅谷的10-20的房价收入比)。 如果说,硅谷的创新,有赖于创业者、工程师、研发人员的想象力、Idea,而深圳的创新,则更主要依赖于研发人员、工程师们的吃苦耐劳、群体智慧。这就是任正非所说的"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工程师的数量比美国多,但成本比美国便宜。虽说价廉物美,但由于两国的制度环境不同,工程师、研发人员的组织方式、研发体制大有不同,当深圳失去"工程师红利"这一比较优势,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保持其创新能力? 或者有人说,深圳可以转向硅谷那样的软件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也就是从1到10的创新。但是这令人深深怀疑,深圳并无硅谷那样天马行空、我行我素、颠覆一切、自由创造的社会环境,也很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像硅谷那样创新?没那么容易。 我们无法判断硅谷这一次能否安然渡过高成本的危机,再次以颠覆性创新改变全世界。也许存在着某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高成本行使着选择功能,让有竞争力的产业脱颖而出,成为本地区的霸主,但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高成本使得除了博彩、金融、房地产之外任何产业都无法在此生存,到那时,也许市场会逼着一个城市向低成本回归。 深圳是否已越过这个临界点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saia.com/shsjd/11711.html
- 上一篇文章: iPhone新机无缘今年WWDC,新版i
- 下一篇文章: 20202021世界顶尖名校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