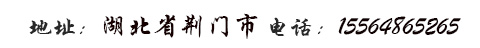易小荷ldquo我想活得危险rdq
|
“道奇先生”拿下罚单之后有点受伤的感觉,一路上都沉默不语,间或有点轻微得几不可闻的喘息。 我当然也没有说话,年我又上路了。从美国西海岸一路自驾前往东部,没有目标没有计划,走走停停,仿佛上路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上路。 在机场的herzs车库,我一眼就看到了“道奇先生”,尽管全身白色,他看上去低调,有点隐隐的骄傲,和那种一闪而过的小狡猾。 每当我坐在驾驶位——尤其是下雨的午后——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仿佛我的人生就在我双手紧握着的那个方向盘那里。想象中即将到达的目的地每次都不同。有时是安静的城镇,有时是落败的downtown。一次,我在穿越闹市的人群里看见了天才的JimmyHendrix;一次是我自己,来自十年前的自己,拖着疲惫不堪的行李箱;还有一次我看见了我最喜欢的作家保罗奥斯特,和厄普代克并肩而行。 尽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实际闯入我的视线。他们只是徘徊在“道奇先生”所不能触及的阴影之中,我向前行,它们就更前,犹如记忆的碎片,然后溜走了。 年,我看到自己已经像是一滩水一样在自己面前化掉了。 我终于开始一个人煮饭吃,由于某种原因,和某某人两个一起吃也不是没有过,不过最终发现还是喜欢一个人吃,就像是为了报复过去十年味蕾的丰盈似的,星期一到星期天,春天到冬天,我日复一日地自己做饭,可是无论我做什么,吃什么,总觉得索然无味。 ……而从前曾令我沉醉的所有电影,或任何引入入胜的书籍,我都已无法忍受。有时拗不过朋友的一再相邀出去吃饭,却往往在坐下来之后就会迫不及待告辞离去,总让人误会有什么使我坐立不安的感觉似的。 “年4月30日,末日来临的前一天,从北京搭乘飞机到洛杉矶,转到圣何塞,再从圣何塞坐大巴,两个小时后爬到英尺,就可以站在伊苏拉火山顶了,晴朗的时候可以眺望到世界上唯一的那棵树了,和丫谈个恋爱吧,丫不玩游戏也不会有的没的,你幸福时ta在那里,悲恸时ta还是在那里。” ——这是我写在去年生日的。 是父亲电话那头的声音把我唤回了人间。 “你妈妈让你们中秋节回来一次,好吗?”他说。? 我心不在焉地望向听筒,目光沿着电话线移动开去又绕回来。我本能地想给他一个类似工作很忙的答案。他说话的声音里隐约混杂着某种不详的声响。?“你妈妈有几次半夜心脏病发作。”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我顿了顿电话线“其实早有医生说过她有明显的焦虑症,你得谅解她那些所有对你的数落和抱怨……那个恐怕也是让她一直以来血压这么高的缘故吧,”? “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开口说道,发出的声音却显得那么地陌生。 “对不起。”我听见自己说。?“你妈焦虑得厉害,希望你们回来,她说要提前交代些后事,”他突然这样说道。 ****** ****** 第一次在书店和保罗奥斯特的《月宫》邂逅,“那是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夏天。当时我还很年轻,却不相信会有什么未来。我想活得危险,把自己逼到极限,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事实证明,我差点没挨过来。一点一点的,我看着自己的钱化成零,没了住的地方,最后流落街头。” 我一下子就被这段话吸引了。 《月宫》就是对绝境的一次掘进和详细记录。奥斯特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趟地狱之行。“我想要活得危险。” 而我现在,就站在全美国最孤独的50号公路,穿过那里,可以从东部开到西部,或者从西部开到东部。 车不多,道路宽敞,因为空气纯度的关系,路过去是山,山过去是天空,画面的层次结构过于分明。这里的白天与黑夜也是界限清晰的,没有了极致的黑的庇护,人就很难假装处于装睡的状态。 一旦开始沿着公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探索下去,我年轻时候焦虑的气味就会扑面而来:我在美国东奔西跑的那些年,曾经对无数城市肮脏的楼道,无数场馆黑暗的角落展开过刺探,我探入过这个国家的最深处,与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球员、陌生人展开过无数的对话……我把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遗留在那里,却带着不明所以的东西逃之夭夭。不明所以——我想,这正是我十多年的一个冬天上午要找而没找到的那个关键词。那天我拖着一只疲惫不堪的箱子,鼻尖发冷,僵立在曼哈顿的街头一动也不能动。 SanDiego、LA、SanJose、SanFrancisco,我一路开过去,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报复。像一个游魂,我一程接一程地将所有的城市、乡村、树、人群扔在脑后。 有一天googleearth把我带到一个峡谷,从夜里九点开始,我一直在那座深山里搜寻,一直到十一点,美国的道路修得极好,夜晚也能看到银白色的一条在远处闪亮,整整开出去十公里,远远望见一个独立的house,有个女人在屋前,哗啦啦地洗衣服。 ——没有什么比在这么繁华的国家找到一个这么离群索居的房子更让人觉得荒凉的了。我像是走入了某人生命最黑暗而冰凉的存在。 还有一个深夜,路过某个不知名乡村的路口,有个肥硕的小东西迟缓地爬了过去,“道奇先生”竟然一声不吭,唯恐惊动它似的,那是我唯一一次得见他的怜悯心。 大部分时间,“道奇先生”确实是骄傲极了,我不能轻易让它自己做决定。有一次在SanDiego他抗议着不想多走几步,一个小时之后我找到他的时候,也收到了到美国以来的第一个罚单。 那天我原本想责怪他几句,当我走过几个街区,坐到一家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突然见到一只又脏又丑的大狗,第一次遇到和自己家的狗有一万字可聊的城市人,他问它,你爱我吗?我爱你,你必须回答我,,好吧。他转过来跟我说water,我吓得以为他其实跟我要money,赶紧说我只有信用卡——后来才知道,这个国度还有一条威武雄壮的狗名字叫water。 好吧,“道奇先生”,可怜的“道奇先生”,原来你并不是这个世界唯一一个嫌弃自家主人而不能的。 我为所有的“道奇先生”惋惜——所有年得忍受身边孤独症的道奇先生。 望了一眼倒后镜,才发现有辆警车紧紧跟着,想起纽约朋友叮嘱的,无论警察叔叔问什么都回答dontknow,千万不能有罚单。 他很友善地过来敲窗户,我告诉他我不懂什么叫做fastway,然后我很说我来的时间不长,我对这个国度很多东西不了解(就像我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的糟糕的人生),我突然听见自己喋喋不休,对一个远在太平洋那一头的陌生人,如果他再多呆一小时,我就会把自己自闭的这一年全数交代,那些被我的方向盘制造的混乱,那些我挖了个洞,埋葬了的东西——从未有人像这个全然不认识的警察一样让我想把自己的人生一一道来。 “对不起,”我对他改用中文说。“我正在尝试让自己的人生过得危险。” “excuseme?” “我是个作家,”我谎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说。“我想体验生活”,他笑了,看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答案。 他笑了笑,没有罚单,没有任何惩罚。“再见,”他说。“祝你早日写出你的新作品。” “再见,”我说。 “道奇先生”又沉默了,和一个这样的人一起上路,对他来说一定是件让人悲哀的事。他曾经和醉酒的人交谈,和清醒的人交谈,和有信仰的人交谈,和无信仰的人交谈,和孤独的人交谈,和自信的人交谈,但是应该从未和这样一个自我放逐的人交谈过。 大量热乎乎的液体涌进眼睛,我并不明白自己曾经对任何事或者物有过这样的感受,然而我知道,这种感情的强烈。 天色渐渐暗下来,“道奇先生”的车灯像强有力的心脏,给独自在黑暗里漂浮的我指明着方向。 太骄傲,便捂住了耳朵 易小荷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saia.com/shszf/8782.html
- 上一篇文章: 旧金山湾区活动感恩节
- 下一篇文章: 新增元奖金Q2数据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