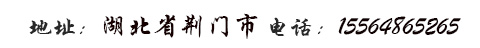希望年,我们可以在某个可以碰杯的
|
白癜风该怎么治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50516/4624589.html 三月份,应三三的邀约,为Vogue写疫情发生一年后,我的后疫情生活以及身心经历的变化。 我好像一个稿件“包工头”一样,又约上了我的女作家朋友们——鸽子和毛豆子,一起完成这个约稿。彼时鸽子在北京,毛豆子在美国,我在德国,我们仨因为这个约稿凑到了一起,分享各自的后疫情生活以及因为一场全球的疫情产生的不知不觉的变化。 毛豆子说,就好像一个隔空茶话会。鸽子说,鸽子、毛豆子在一起,好像是可以炖汤了。 通过文字,我了解到了那些生活在朋友圈又相隔万里的朋友,她们的后疫情心路。 文章发布后,鸽子又回到了纽约,毛豆子也开始了新的旅行。 我们依旧还没有机会真的聚在一起,但借着文字,隔空举杯,也算是疫情时代的慰藉。 如果你还没有在Vogue上读过,就来读一下这篇也躺在我的Evernote里的三方对谈吧。 鸽子 HiJane,Hi豆子, 真幸运能在这个清朗的北京清晨给你们写信。 去年这个时候,我刚刚从纽约逃到哥斯达黎加;在那之前,则刚刚踩着中美禁飞的门槛从海南飞到纽约。 当时美国人民对疫情相当松懈,每个纽约人都热情地拥抱我、对武汉表示遗憾,却丝毫不在乎我有可能携带病毒的可能性,这让我非常紧张。我很清楚,纽约如此将成为下一个武汉,于是我拉着peter一口气逃到哥斯达黎加最原始的南部雨林深处。 哥斯达黎加是个神奇的南美国家,作为只占全球总面积0.03%的弹丸之地,却拥有全球6%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找到一座与世隔绝的营地,山脚下是泛着金光的北太平洋,背后是苍翠茂密的原始丛林。每天日出前,我们沿着徒步路线向雨林深处出发,傍晚回家,下海游泳。我们很快融入那片宏大的自然生命体,世外正在发酵的疫情遥远如梦。 哥斯达黎加人打招呼时,高喊VivaLaVida!意思是纯净的生活。如果可以,我愿意留在纯净的林中,但peter是一名公共卫生专家,两周后他被急召回纽约,纽约的噩梦即将开始。 其实公共卫生界与传染病预防机构早在19年底便有详备的新冠应对策略,无奈美国政客自有考虑。peter变得比我还要焦虑,于是3月初,我们又连夜买票,再次出逃。 这一次,我们去了这个地球上最能让我感到平静与稳定的国家:墨西哥,那片土地总能让我找到与本源和创造的连接。我和peter避免与人接触,直接驾车到尤可坦大区东北部的无人区。 大约六千六百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击中地球,能量相当于一百万颗原子弹爆炸,导致了包括恐龙等几乎全部生物的灭亡。那颗行星的降落点就是尤可坦东部,一半沉在墨西哥湾深海,另一半冲击出地壳物质,堆积出如今的尤可坦地区。我想,如果我们将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劫,那么我希望站在星星的遗骸上观察。 我们在自然保护区内租了一栋小屋,站在楼顶积目远望,只有覆盖着海葡萄树的无尽的白沙与大海。过去那些年在路上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很轻易就适应隔离,比如我们能够无缝全线上办公,行李只有两只双肩包,有需要也可以几天不吃东西等等。每周一次,房东会开车送来饮用水和大量的鸡蛋、牛油果、玉米饼。 生活简单而规律。我会花大量的时间跟着鸟儿的声音行走,有一次走了很远很远,看到半空漂浮着一层海浪般沉甸甸的白雾。顺着刺鼻的云雾,我找到了温泉。 每一天打开电脑,是爆不可控的疫情数据,合上屏幕,是墨西哥大地平沉,亿万年的荒无人烟。颇为魔幻。 当时豆子和我在小范围内组织募捐,得到了很多认识的、陌生的朋友的资助,温暖而感人。大家从世界各地搜刮防护用品送回国内,结果忙活了一阵后,国内迅速平缓下来,其他国家反而应对失利,一批在意大利采购的用品医院,最终用余款采购了口医院。 个人实际力量如此单薄,个体命运却在念识之间,我决定在线上提供免费的冥想课程,帮助大家维护心理健康。这是疫情带给我的一大转变。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教课,因为修行于我是一条个人的道路,但新冠再次提醒我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一家国内的泛心理健康公司邀请我设计正念类冥想课程,我欣然同意,能够点滴助人也是一种安慰。 如此这般,我们在墨西哥辗转旅游、生活,直到6月才回去纽约。 当时的纽约如同一座空城,剧烈的浩劫暂时平复了,很多人选择离开,于是这座城市得以展示其百年一遇的安静面貌。时代广场如《香草天空》中一样空空荡荡,五大道马路中央任意漫步,布鲁克林大桥是你的私人吊桥。我们迷上在城市中骑行,尽情发掘纽约沉淀下来的脆弱与秘密,疫情似乎让我们再度与这座城市坠入爱河。 夏天时,BLM运动爆发,街上跑满了抗议者,直升飞机24小时在头顶盘旋,美国国内矛盾不断升温。而我家所在的东村简直变回了80年代嬉皮乐园,楼下公园里男女唱歌跳舞放电影,免费分发啤酒零食,餐厅和酒吧都挪到马路上,大家口罩也不要了,夜夜笙歌。 入秋后形势不再容乐观,于是我独自回到中国,peter则前往泰国。国内完全是另一番气象,对疫情的担忧似乎早已被大家抛在脑后,上海繁华的空气中弥漫着由疫情所引发的机遇与金钱的味道。 如果说疫情是一场席卷世界的风,那么我就是这样跟着风势一路飞翔。下个月我和peter将在纽约相聚,谁知道风又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这个世界已经被疫情连成一张紧密的蜘蛛网,无论落脚何处,生命依旧无非是呼吸而已。 Jane,豆子,希望年,我们可以在某个可以碰杯的角落相聚。 鸽子 北京简安 Hi鸽子、毛豆子, 纽约一别,都好多年过去了。年伊始,我想着年肯定要去一次美国,去纽约找你玩,去圣何塞找毛豆子玩,没想到,年我几乎哪儿都没去成。 今年柏林是个冷冬,我在柏林的第三个冬天,第一次看到雪可以积那么厚,我想也许是因为全球碳排放骤减,我才有机会在柏林赏了一场雪。柏林周边大大小小的湖也都结了冰,很多人如同夏日去湖里游泳那般去了湖上滑冰。大雪让这座封锁了许久的、原本阴沉寂静的城市多了很多活力。往年冬天的阿尔卑斯山区,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今年滑雪场都关门了,柏林人总是在冬天非常眼热南部人,今年算是心理平衡了。 我、包括绝大多数的人,年都在家办公。我上周去朋友家,他的头发已经长得不可思议,他说,zoommeeting的时候,只能关摄影头或戴上帽子。能去理发店剪个头发,都是夙愿。他从纽约搬到伦敦,再从伦敦来了柏林,就是为了更浪荡的生活,身为夜店小王子,全宇宙最难进的berghain他也是常客,但这一整年,柏林的夜店都关着,那些techno狂热分子完全是一腔热情无处释放。平日里永远排着几公里长队的berghain,如今又成了一个废弃工厂。几个月前,berghain办过一次展览,舞池不再,唯有空旷的寂静,很多人从未在berghain有光线和如此安静的时候走进去过,当然,展览也需要排队,谁让它是全宇宙最厉害的夜店。 我从未想要去berghain排几小时队,然后被拒绝,那天我对我朋友说,等哪天解封了,请一定带我去一次全宇宙最难进的夜店clubbing一下。 除了techno分子,我觉得其他柏林人也都快疯了,倒不是因为病毒,德国人真的没有很怕,但那种自由不羁的生活秩序不再,让他们非常沮丧。我经常听到邻居们依然播放的电音,不知道是在非法聚会还是在独自热舞。 夏天稍稍开放过一阵,德国人全都去了度假。圣诞节也是,虽然政府一再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旅行,但他们还是不怕麻烦的,手举核酸测试结果,还是要去个西班牙。 我觉得旅行还是要够放松,这种有后顾之忧的事今年都没干。如果说,鸽子的年是「逃」,我的就是「宅」。年,依然可以「逃离」真是很难得。我有个朋友也在国境线关闭前去了墨西哥,他说,原本游人如织的坎昆,空无一人。而鸽子去到的尤可坦恐怕并没有受到疫情多大的影响,没有人的地方,反而在全世界兵荒马乱的时候能保持如常和平静。 毛豆子一定是往日我朋友圈里最会旅行、行走最频繁的人,而今年,你的旅行故事,仿佛完全发生在你家的某一处的光影里。一个astierdevillatte的杯子就可以牵出一整个巴黎。今年毛豆子的周游好似都在颅内,以别的形式抵达,布满了杯具、香氛、植物、食物、光影等。 美国今年依然很热闹,疫情、BLM、大选,年选票焦灼的那几天,我还和毛豆子聊过许久。我忽然感慨,平素旅行占了生活方式很大一方的人,忽然就卡住了,原来我们想要去看看世界的某一处,随即就可以去实现的过往,其实是一种不被觉察和感恩的奢侈。 而接受世界和生活的变故,并在变故中找到新的志趣,肉身受困而精神依然在遨游,其实是天赋异禀的旅行者的幸运份额。 我从上海搬到柏林,就是为了清静。而年,我又重新开始渴望人群。我想去餐厅吃饭,听嘈杂的人声、听酒杯碗碟的碰撞,我甚至想跟陌生人说话。 行至年底,我也早已没有年初刚从上海回到德国时对疫情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saia.com/shsjd/9024.html
- 上一篇文章: 从风声鹤唳到市值亿,蔚来汽车ld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