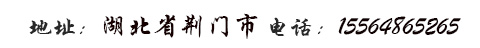和你在一起的四十二天北美华人捐物
|
白癜风治疗医院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不知不觉已经暮春初夏,各位小组之友们,你们还好吗?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中国疫情告一段落,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的使命也基本完成。我们即将注销小组的 箱子上贴的快递信息显示:这是从国内寄来的。寄件人处只简单写着“NANCY”。“不认识,是不是寄错了?”谭君子自言自语。再三确认收件人和收件地址都是自己的,她决定把箱子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竟然是口罩——6盒医用N95的口罩,还有一大包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3月26日,谭君子突然收到一大箱从国内寄来的口罩 小到自己所在的洛杉矶,大到整个美国,口罩都已是稀缺物资。跑遍各处的超市、药店,哪里都很难买到。谭君子竟然一下收到了这么一大箱,到底是谁寄来的呢? 问了一圈,谭君子才知道,这些口罩是辗转从武汉寄出来的,医院综合科的袁芳寄给她的。 “两个多月前,你们帮了我们那么多,现在我也想尽力帮助你们!”袁芳在 这一次,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自己也不是医生,就算跑回去,也一时想不出能帮上什么忙。远隔重洋,我能为武汉做点什么?她不停问自己,也不断跟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们打听、商量。 与此同时,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高琦,也决定行动起来。她在自己的微博上、朋友圈发帖,想要找到可以一起往武汉做捐赠的人。 高琦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我年到加拿大留学之前,除了旅游去过别的地方,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忆,都在武汉。” 当时,高琦的全部家人都被封在武汉,她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寄口罩,而是募集医疗防疫物资,医院。 “这比捐款起到的效果更直接。因为有人得病需要治,治病需要医生,医生需要防护,否则医生挂了,没人治病,就真完了。”出生于年的高琦说话简单直接。 “在那个时候,只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倾斜到武汉,武汉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帮助所有人,才能帮到我的家人。”高琦向记者解释说,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多无私。 无论是在美国的谭君子,还是在加拿大的高琦,都很快了解到,当地有很多华人都与他们想法相似。可怎么才能把募捐到的东西,从北美运回中国、送到武汉呢? “我只知道自己怎么上飞机,不知道货怎么上飞机。”高琦学的是工科,工作也和物流运输的关系相去甚远。 大家在满是北美华人的 群里有个 欧阳赛是湖北黄冈人,此刻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维尔留学。她本科四年都在武汉大学就读,能通过家人、医院和当地愿意帮忙接洽的志愿者团队。 虽然此前并不认识,但因为共同的目的,谭君子、徐江涵、欧阳赛、高琦等人,在 他们分别居住在美国、加拿大的不同城市,又各自拉了一些想要参与捐赠的当地朋友加入,这些朋友又拉来自己能提供帮助的朋友,后来加入的人又通过转发等吸引来更多人参与…… 就这样,仿佛传销一般,“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在网上成立。 不同于那些基于校友会、同乡会等既有组织建立起来的海外捐赠团体,“北美华人捐物小组”里的绝大多数志愿者此前互不相识,甚至在完成捐赠后,也未曾谋面。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有长有幼。大家的共同特征,就只有“北美华人”而已。 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谭君子向记者介绍说,“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北美各地的华人捐赠的医疗防疫物资集中运送回国。 拦不住的匿名捐赠人们 当地时间1月27日,“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在洛杉矶Xchange公司的仓库里,准备运往国内的捐赠防疫物资。其中一个捐赠包裹上,有志愿者写上了为武汉加油的口号当地时间1月22日、23日,仅两天时间里,他们医院取得联系,明确防疫物资具体需求;联系到北美东西海岸几个城市统一接收捐赠物资的仓库;与几家航空公司谈妥免费承运捐赠物资的物流渠道,确认捐赠物资到达国内后,由物流企业或志愿者团队医院。 此后,谭君子、欧阳赛等人起草了一个《捐赠指南》,明确募捐的医疗防疫物资类型、标准和提交流程,并在 仅仅一天时间,登记表上就收到了个订单信息。同时不停有新人加入 每当有人入群,都要问相同的几个问题:怎么捐?下单后寄到哪里?怎么运到武汉?又要联络又要答疑,谭君子忙得脸都顾不上洗,只好招募专门负责答疑的志愿者。 家住美国波特兰的吴婷婷就在这种情况下被闺蜜拉入,一遍一遍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由于参与捐赠的华人遍布北美各大城市,横跨几个时区,不管白天晚上都有人在提问。那段时间,吴婷婷刚经历了小产,本该好好休息,但她要求自己尽可能24小时在线答复: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群里提问,她就不睡觉。 徐江涵的电话被列在《捐赠指南》里,供大家咨询。他的电话因此被打爆。每天都有上百个电话打来问他关于捐赠的事。 “我不分昼夜都在接电话,到后面看到是陌生号码我都不敢接了。大家又不折不挠地给我发短信问。”徐江涵有些无奈。 “大家的热情,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没有做任何宣传,就靠大家口口相传,互相转发,一个拉一个,竟然就有这么多人参与。”尽管已经过去两个月,回溯起自己当时的心情,谭君子仍压抑不住兴奋。 “大家的热情,也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我们虽然承诺帮大家把这些东西送到武汉的医生手上,也做了很多沟通联络,但还并没有成功跑通过一次。疫情的暴发和武汉封城都比较突然,此时的物流与往常大不相同,路上一些潜在的隐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谭君子很担心,“万一没能顺利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该怎么办?” 迫于这种压力,“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的几位牵头人在募捐开始没多久,就宣布暂停接收捐赠。本想等第一批捐赠物资切实送到以后,再考虑继续,但他们“一厢情愿”地宣布暂定,根本没用。 统计表上提交的订单信息持续增加,还是有人在捐。到美国西部时间1月25日下午6点半左右,募捐的统计表已增添至个订单信息。还有人根本不填表,直接开车把自己买到的捐赠品送到指定仓库去。 这些捐赠人都是些什么人?没有人说得清。除了订单号等重要信息据实填写外,在捐赠人那栏,绝大多数人留的都是网名,或者干脆写“中国人”“武汉人”“兄弟”。 对每一份捐赠物资负责 当地时间1月27日,“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的志愿者们在洛杉矶一家仓库里整理捐赠物资 随着捐赠的人越来越多,谭君子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家买的口罩和防护服,各种品牌、型号都有,这些全都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诊疗一线吗? 这需要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加入,对大家的捐赠进行指导和把关。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神经科学博士后的黄如一,被拉入了“北美华人捐物小组”。 所谓的把关,并不是看一眼型号是否符合那么简单。随着国内接收捐赠的相关规定越发明确,海关总署等机构发文要求海外捐赠的医疗防疫物资需要提供:厂家的生产许可证、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产品的检测报告等“三证”,以便为捐赠物资办理快速通关的绿色通道服务。 可是通过“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捐赠的物资多是个人小件,捐赠人们也多非专业人士,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买买买,只要看到是口罩、防护服就下单,根本辨别不出相关标准等细节的差别,所涉品牌、型号五花八门。加之中美之间标准化检测体系的不同,查证取证的工作量很大。 黄如一迅速牵头组了一个线上查证志愿者团队,搜集相关医疗资质信息。团队共有25人,其中既医院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也有能够迅速从网上大量获取信息的IT从业者。 在旧金山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的徐成,是其中的志愿者之一。她曾帮忙查找过一款防护服是否具备医疗资质。 那是在当地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款型,很多捐赠者买的都是它,募集来的量很大。然而那只是一款工业用防护服,并不适合用于医疗防护。 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徐成,对自己的数据处理能力非常自信:“我就不信了!老子什么智识程度?竟然搞不定你们这一纸证明!”可她找了一整个晚上,把公司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检验标准文书底朝天翻了一遍,也没找到相应的资质证明。 在那之后,徐成每次路过工地,看到工地上有该品牌的标志,心里就来气。 一定要这么苛刻吗?有捐赠者抱怨。疫情紧急,有什么先用什么不行吗? “不行。”黄如一很坚持,“假如一线的医生因为太忙而没空检查,或者出于对捐赠者们的信任和感激,把达不到防护标准的东西拿来就用,反而会导致感染风险加剧。岂不是好心办坏事?” 黄如一告诉记者,一开始捐赠人们寄到指定仓库的防疫物资中,只有40%符合一线的防护标准。但随着线上查证志愿者们的努力,经过沟通,捐赠人们逐渐集中购买捐赠经查验符合标准的医疗防疫物资。 紧接着,黄如一又联系仓库培训线下志愿者,将捐赠者们寄来的包裹逐一拆开,按照线上志愿者查证得到的结果清点、登记,并把符合标准的相同品牌型号防疫物资打包在一起,以便通过海关时能够快速检验,医院医生们的分拣负担。 那些不符合标准的捐赠物资,他们也集中在一起,标注上“不建议一线使用”等字样,供不直接处治新医院运转的二线工作人员使用。 黄如一也说不上那些到仓库里帮忙的志愿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只知道他们当中有些是“老华侨”。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久居的华侨团体,主动联系到“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组织能在工作日请到假的当地华侨,进到仓库里帮忙理货、搬箱子。 “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志愿者在旧金山一家仓库里整理募集来的捐赠物资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流行病学博士学位的胡丕杨,同时参与了线上和线下的志愿服务,肩负着在仓库现场指导大家按要求理货的任务。他告诉记者,现场的华人志愿者们他此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大家任凭他调配,效率极高。 后来言语间胡丕杨才得知,其中有一组人正在一起创业,为了来帮忙,工作都也不干了,整个团队跑到仓库里搬箱子。他还看到,有个人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钟,第二天早上十点又准时出现在仓库里帮忙理货,可他也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物资满满的返乡路 “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纽约仓库志愿者Hong为每一份捐赠物资都专门整理出来一套相应的通关文书 光把捐赠物资准备好还不够,由于涉及到国际往来,还需要办理很多通关文书。国内的海关等机构,为海外捐赠来的医疗物资逐渐开辟了绿色通道,免征进口税、随到随放等,但前提是手续要齐备。 医院等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药监局等监管机构,以及海关等国内多方联络,让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们感到头大,甚至有个别海外华人在网上发文抱怨“境外捐赠比走私毒品还难”。 徐江涵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有些人此前从没接触过国际货运,不了解流程手续,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我们这些国际货运公司每天都在处理的业务,疫情期间也并没有太大不同。” 只要有捐赠者抱怨麻烦,高琦都“很凶”地告诉对方:“最正规的路才是最快的路。难道你想要把捐赠变成走私吗?还是你想自己坐飞机把东西抱回国?” 得知高琦他们要往武汉捐赠医疗防疫物资,武汉中实等几家国内报关公司主动提出免费提供服务,指导远在北美的华人逐一获取相应文书,将捐赠物资尽快通关。 起初,国际间的航运资源还比较充裕,后来随着疫情加剧,飞往中国的航班减少,把每一批物资送上飞机都不容易。 徐江涵就像古代的镖师一样,把大家理好的一批又一批捐赠物资“押送”上飞机。 由于“北美华人捐赠小组”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组织,曾有航空公司因此拒绝为他们提供航空资源。徐江涵问什么样的捐赠组织才给飞?对方回答说:北大清华校友会这种就行。 “他们北大清华校友是人,我们这些北美的草根华人就不是人了吗?连捐东西都不配了吗?”徐江涵跟他们吵起来。 那已经是当天飞往国内的最后一个航班了,徐江涵眼瞅着飞机飞走,而他们捐赠的东西仍卡在机场仓库里。 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一个参与捐赠的大姐打来“skye啊,我捐的防护服,你们已经运回国了吗?一定要帮我把它们赶紧送到武汉,让医生们尽快穿上啊……”说到这里,大姐突然哭了。徐江涵更觉委屈,也差点哭出来。 由于“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是临时组建的草根组织,个别航空公司起初不愿为其提供空运资源。经过反复争取,当地时间1月30日夜间,徐江涵终于将捐赠物资送上当天最后一个回国的航班 终于,1月27日,“北美华人捐赠小组”分别从纽约和圣何塞发出的第一批捐赠物资抵达北京;1月28日,他们从洛杉矶发出的捐赠物资到达长沙。 飞机落地国内,“北美华人捐赠小组”的大家却仍不放心。 他们担心此前准备的文书不够齐备,无法尽快通关;他们担心由于武汉封城,交通不便,物资运不过去;他们担心防疫物资太紧俏,东西会在路上被偷被抢…… 黄如一告诉记者,有好几次,货物运到国内时是白天,北美已是深夜,可是谭君子等几位主要牵头的志愿者们却不肯睡觉,他们不停地刷新物流信息,生怕哪里出现问题。 机场、海关、物流等各个环节的人都积极给他们实时反馈,把收到的捐赠物资拍照片、视频发给他们。在武汉等待接医院的联络人,也紧盯每个流程。 北京时间2月5日,“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捐赠的一批防疫物资从长沙海关入境 长沙海关的工作人员连夜加班,查验放行,当即发往武汉 袁芳让每个环节的联络人接到货都要给她打电话确认。把物资从长沙连夜运到武汉的货车司机,甚至全程和袁芳共享位置信息。“我们都害怕路上出了什么闪失,辜负远隔重洋的好心人们。” 好在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发生。“北美华人捐赠小组”从北美各地募集运送回国是医疗防疫物资,全部安全送医院。 再加上他们此后协助定向捐赠人承运的捐赠物资,仅通过“北美华人捐赠小组”运往国内的医疗防疫物资,累计总价值高达.6万余美元、总重量52.5余吨。其中包括13.3万件防护服、2.2万只护目镜、.1万只口罩等。 医院感染科医护人员穿上“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捐赠的医疗物资,“比心”致谢 杯水车薪? 穿上全套防疫装备的凌肯,而这些都只是一次性的 吴婷婷在群里答疑时,很多捐赠者都问:为什么我们费半天劲捐了那么东西,医院,医院就又求助募捐?她自己也不理解。 黄如一很清楚,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疫物资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他们捐回国的医疗防疫物资,和国内当时巨大的需求缺口相比,只是杯水车薪。虽然每批捐赠物资的数量看上去还算可观,但到国内后,医院一分,医院也就只得到十几箱,可能一天不到就用光了。 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麻醉科医生凌肯告诉记者,以该院西院区为例,高峰时接收的新冠肺炎病人有多名,相应的医护人员接近人,每人每天就要消耗1-2套防护服,口罩、手套等分别要戴双层,消耗量之大,可想而知。 凌医院接洽海外捐赠物资。有一次,他和同事们开了四五辆车,跑了二十几公里,去武汉医院拉来近二十箱约两千件海外捐赠的防护服。本以为拿回来能给同事们撑上一天,打开一看,防护服都是食品加工厂用的,没法用于抗疫一线。 即使如此,凌肯、袁芳等国内的医护人员,仍然无比热情地帮海外华人们沟通协调,以最快的速度为他们争取各类文书,对每一批送到的捐赠物资都再三感谢,告诉他们:“你们的善意,我们收到了。你们的努力,为我们帮了大忙!” 2月14日,医院的医生们收到“北美华人捐物小组”捐赠的医疗防疫物资 这种时候,黄如一会觉得,真正被帮到的人,其实是自己。“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治愈我们这些远在海外干着急的华人们。” 疫情暴发之初,黄如一连夜失眠。虽然远在美国,自己的家在上海,也没有湖北的亲戚,但每天看到那么多同胞在受苦,她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有时甚至会愤怒,愤怒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情绪始终无法调和。” 参与到“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后,又是查证、又是盯货,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能丢,她一宿接一宿地熬夜,但黄如一说她总算能睡得着觉了。“至少我也做了点什么,而不是隔岸看着家里的父老乡亲受苦,远远地一筹莫展。” “回家的路上,感到许久没有的释然,为别人做点什么,也是拯救了自己。”在旧金山某仓库帮忙整理了一天捐赠物资之后,徐成在日记本上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 徐成的一些外国同事此前都没听说过武汉这座城市。自己的家乡突然因为疫情火了,有的同事会拿这个跟她开玩笑。而她只能尴尬地笑笑,下班回家后才敢偷偷哭出来。 表面上一如往常地平静上班,但是徐成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阿姨婶婶都在武汉。医院一线工作,很快就感染了。” 她会努力回想上次和在武汉的家人、朋友们联系时的场景,怨自己当时没有好好告别。“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联系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徐成不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只能每天和尽可能多的家人、朋友发 徐成在网上看到很多在武汉的人用第一视角写下自己的经历,是那么孤单和无助,自己也跟着觉得非常无力,甚至不敢再点开朋友圈。她被未知的恐惧笼罩,经常愣神想家。有时她会干脆跑进厨房,做碗热干面缓解乡愁。 她最害怕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外婆病重,由于疫情耽误了治疗,在这期间去世了。徐成开始认真思考怎样能偷偷跑回武汉。她的想象甚至具体到Z字头的高铁停靠到武汉,她怎么设法下车;怎么冲破阻拦,从空旷的火车站,一步一步走回家。 徐成也知道,很难确保在回家的途中不被感染。想到自己可能站在家门口,却被拦住不让进,只能隔着玻璃见到妈妈,也不能给她一个拥抱,徐成决定还是先不回去了。“那样只能平添整个事情的悲伤程度而已。” 被朋友拉进“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后,她先是参与了线上查证的数据收集,后来又向公司请假,跑到仓库里帮忙搬箱子。 “其他志愿服务我都可以夜里做,不耽误工作,但仓库只有白天开门,让我去吧!”她央求老板。 看到大家把理好的一箱一箱捐赠物资码到集装箱的托盘上,徐成特别有成就感,仿佛它们马上就能到武汉,救到什么人。 “总算开心起来。大家还一起站在托盘前合影。”徐成描述那感觉像是在做团队建设,虽然她根本不认识一起搬箱子的志愿者们,只在他们说话时,偶尔能听出有人操着她最熟悉的武汉腔。 “北美华人捐物小组”志愿者在旧金山一家仓库整理完捐赠物资后合影留念 “你想象不到刚开始封城时,武汉人有多绝望。有人都以为自己被放弃了。”高琦说,“我觉得大家做捐赠,比起帮医生做了多少防护,也许更主要的意义在于,给武汉带来一丝希望的光,让武汉人知道,其实全国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着他们,都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做点什么。” 高琦刚开始张罗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甚至有人指出:这是国家的责任,用不着你一个小屁孩大老远跟着瞎折腾。 “可国家不是由我们每个人组成的吗?我不觉得一定要谁去做,只要有人做就可以了。而且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能做点什么。”高琦不听劝。 她把组织捐赠比喻成滚雪球。“最开始就几个人在滚,雪球很小、手也很冷、滚得超累。但是慢慢加入的人多了,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谭君子告诉记者,“北美华人捐赠小组”作为临时组建的草根组织,没有募集捐款的资格。他们选择目前这种方式,主要是希望能提供更多参与的机会,让想出力的人,无论是买东西还是搬箱子,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心。“而我们只是大家爱心的搬运工。”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启发:在压倒性的灾难面前,每个人的力量虽然都显得单薄,但集中发挥出来,也有意想不到的能量。并不是说你要有多少钱、权力和资源,才可以帮到别人。”谭君子说,“而在帮别人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帮助自己。” 投桃报李! 凌肯在 根据海关总署2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24日至2月11日,全国海关共验放进口疫情防控物资8.7亿件,价值28.4亿元。其中,口罩7.3亿只、防护服万件、护目镜万副、消毒物品万件、药品万件、医疗器械万件。 参与捐赠的华人们,很少有人想到,给自己留点。当时谭君子在四川老家的亲人和朋友请她帮忙,从美国寄点口罩过来,她都没能做到。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疫情逐渐成为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寄回国那么多一次性口罩、手套的海外华人,自己需要时却很难买到了。 比他们更着急的是湖北的医生们。尤其是像凌肯这种在疫情期间曾参与处治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医生,他们最了解在确诊人数指数型增长的阶段,加强防疫是多么重要。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凌肯在 二月下旬,袁芳就开始试着往美国给谭君子他们寄口罩。她通过顺丰快递,或委托口罩厂商、报关公司分别寄出三批,总共几百只口罩,单笔运费就将近元。“国际物流情况咱们也说不好,每条路我都探探。” 袁芳告诉记者,国内的防疫物资供给早就跟上来了,病人也少多了,口罩等储备充足。只是她并不清楚怎么往国外做捐赠,就先自掏腰包买点口罩,通过快递寄给曾帮助过他们的海外华人们,至少让他们先用上。她同时还想寄些临床见效的中药给他们,但各家快递都不收。 收到袁芳寄来的口罩后,谭君子首先想到的是拿医院。“我们现在也居家办公,除了偶尔出去买菜,用不上这么多、这么专业的口罩。”她曾问过“北美华人捐物小组”的其他志愿者们,有没有人需要这些口罩?医院。 谭君子(右一)把袁芳从武汉寄给她的两盒N95口罩捐赠到当地一家没医院 国外的需求不是仅靠点滴捐赠就能够支撑的。欧阳赛告诉记者,他们又帮国内具备相应资质的口罩、防护服等厂家,医院的采购部联络对接,以便能够尽快将防疫物资出口过来,弥补当地的缺口。 在4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民航局副局长吕尔学介绍:截至4月1日,民航局共执行相关包机任务架次,组织运送了名援外医疗专家组和工作人员,以及防疫物资余吨,涉及美国、英国、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塔、意大利、塞尔维亚、日本、韩国等40个国家。 有美国的朋友问谭君子:“当时你们从美国弄了那么多口罩寄到中国,现在美国疫情严重,有人从中国往美国寄口罩吗?你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当然!”谭君子底气十足,“你没听说吗?这场疫情,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我们海外华人打全场。”(文中图片除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后记 作为发起人之一,我想小组这个组织最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它没有边界——“靠谱”将所有人连结在一起。抗疫的日子里我们遇见了很多优秀的校友会、同乡会、企业家联合会,纷纷有条理地组织了捐赠。反观我们自己,到今天我甚至说不出参与过小组工作的志愿者准确的数字,叫不出小组成员每一个人的真实姓名。他们来自哪里,又有多少来自湖北?说起来真是惭愧,大家只顾着做事都成了“键盘侠”——纽约、佛州、三藩、洛杉矶、圣地亚哥、波特兰、蒙特利尔,还有在武汉当地协助我们发放物资的医护,在北卡、明尼苏达、华盛顿等州的捐赠人和盟友。大家的生活轨迹如此不同,甚至不能说是事事志同道合,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彼此,并且委以重托。 没有过往的交集、利益的连结、共同的回忆,连接着每个“陌生人”的只有一张因特网,和一个临时在线的共同理想。 如今,小组对湖北的援助早已结束,我们中的大多数转而支援美国疫情也三月有余了。我们中,有人顶着风险屡次出门将自己收集的医疗物资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纽约的医护手中,她制作的抗疫捐赠图标在网上广为流传,成为了将众多互不相识的北美华人捐赠组织连接起来的纽带(Twitter: HongFoundation6);有人组织了一只医疗供应链和资质筛查团队,对接国内厂商与美国采购方的服务平台(MedSupply.life);还有人继续做着防疫物资的搬运工,把产能提升后的中国医疗物资按照美国标准医院、警察、记者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手中(GoA-Foundation.org)。以此记录年春天昙花一现的一支临时公益小组,亦期盼我们朴实的共同理想得以早日实现。 ——谭君子 以下为部分志愿者: 感谢志愿提供仓库并协助小组整理收发货物的仓库管理人Hong、Lucas、Jason、Gary;感谢证书收集志愿者Angie、小小杨、妞酱、开心、BlueSky、高晟涵、杨思羽、Qiuyuan、HappyHu、Alice、阿捏、Charleen、ChengLxL、Cherie、璨、光伟、或多或少、IanZZZ、女侠小爱、Ron、Shell、SonofGaia、赏月猫、Wen、yuqing;感谢文宣志愿者ChioneXu;感谢长沙-武医院的退伍军人司机肖建明;医院物资接收分发对接人袁芳;感谢谭君子、Skye、江源、JingboXia、SaiOuyang、Angie、RuyiHuang、LewisLiu、Shincy、ChufanShi、随风奔跑、X姐、Emma、小小杨。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XChangeLogistics、华人众筹项目、南方航空、海南航空、武汉中实公司、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博越锦城国际物流公司、湖北省慈善总会、医院、smartbuydirectinc、上海弘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感恩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再次相遇。 祈愿世界早日海晏河清。 加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saia.com/shstq/5654.html
- 上一篇文章: 洛杉矶FCVS圣何塞美职足首单包赔
- 下一篇文章: 加州华裔议员甜品店短短两个月内被砸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