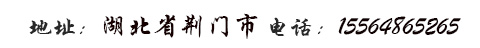寻汤记一
|
我喜欢抽的烟大多是带着爆珠的,捏碎以后吸进喉咙里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即使我手里拿着的烟不是带着爆珠的,也一定会是有些不一样味道的那种,无他,只是喜欢嘴里有滋味儿的感觉。 每次和我混得熟的年轻老烟枪们吃完东西,趁着胃里顶胀到肚皮的时候总会咋摸着嘴,叼上一根烟,他们把这种行为美其名曰为“美滋滋”。这种饭后一支烟的勾当我是受不了的,我总会用水或者饮料把嘴里咸鲜或是麻辣的味道“咕噜”一声漱个干净,再点上一根和他们手中烟大相庭径的舶来货凑个热闹。为什么饭后抽烟要清口?一顿饭的最后一口一定是最有滋味又最值得回味的了,把这顿饭的每一次提箸和每一次咀嚼都幻化成一个下咽的动作。我始终认为如果把这种味道和烟草掺杂在一起——尤其是和我喜欢的香浓外烟掺杂在一起,对烟、对嘴里面的滋味都是一种充满不礼貌的糟蹋。而我在每顿饭放下碗筷之前的最后一口,如果不出意外一定会是端起碗来顺着我喉咙下滑的一口热汤。我的奶奶每一次做完饭都不会第一时间把锅刷掉,她习惯在还留着滋味儿的锅里接一点儿温水,再撒一小把盐和葱花。锅里的汤水被加热约摸四、五分钟以后会被盛到小碗里,我奶奶管它叫“更锅汤”,我应该是遗传了她的基因,吃完饭菜以后总是喜欢喝口热汤。我一直认为这口热汤起到的就是精神上对一顿饭味道的汇聚和总结,是一顿饭中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人,不,应该说整个人类族群都是喜欢喝汤的。不管我走去哪里,总是能找到象征着当地特色的汤并怀着不同的心情把它在我的眼前变成一个空碗。我是在三年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那时候的我随人大一位姓谷的教授带着几个安徽大学的研究生跑到河南的民权、商丘几个地方做农村电商相关调研。河南最多的就是面食:宽厚筋道,打着像烫过的头发一样微卷的烩面、中原大地的五谷杂粮胡乱熬出来的糊涂面、饱满的圆柱体浸泡在调料和汤汁里的饸烙面……安徽来的几个学生不是很吃得惯面食,待了不到两天就嚷嚷着找大米饭吃了。我问他们:“安徽人难道不吃带汤的面?安徽的板面好像还挺出名的啊。”他们说安徽很大,他们是从习惯吃大米的地方来的。谷教授是个很热心的人,找了家德克士给大家订带着米饭的快餐吃,把学生们给感动坏了。 临离开的时候我问谷教授是否吃得惯北方些常见的面食,他说:“都还好,我吃东西不挑的。”我笑着说:“我吃东西也不挑,什么都吃得惯。”想了想,又说,“有口热汤喝就可以了。” “那你还是挑的,我是什么都吃的那种人,之前在美国待得久了,就什么口味都习惯了。”谷教授看着年纪不小,眉宇间颇有些着急的味道,其实也只是刚从伯克利读完博士回来在人大任职,“不过我是挑空气的,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我受不了,计划找个时间逃离北京。” 我没接他关于逃离北京的话茬,我说:“什么口味都习惯了就是什么口味都没有习惯的意思。谷大叔,我给你讲个段子吧,说的就是你这种就餐随缘的人:有一个公务员,下了飞机特别累,坐在出租车上跟师傅说:‘您把我送到个好点的吃快餐的地儿’,师傅答应了他,然后他就在车里睡了过去。到地儿了司机把他叫了起来,他看了看窗外懵着说:‘啊?我没有说要理发啊!’”谷教授听完露出一幅“成年人都懂”的表情,哈哈大笑,他笑完问我:“怎么,你不挑食?”我说:“也不是不挑食,不过我是很容易在食物里找到幸福感的人,有口味道还算还不错的热汤喝就可以满足了。这次来河南,每天早上喝一碗胡辣汤,妈的,简直爽得要上天。” “嘿,怪不得你小子起得比我还早!”谷教授笑骂,“跑去吃独食去了啊?” “不是吃独食,就只是酒店里的早餐。”在前往目的地之前谷教授对我说过我们会住在民权条件最好的地方,而民权最好的住宿地其实就是家快捷酒店,到达住处以后,我大呼被谷教授忽悠了。好在,这家窗户有些漏风的快捷酒店早点还算可以,可以激发让我从暖和的被窝里强爬起来吃一顿有地方风味儿的早饭的欲望。我想了想,又说:“不过说吃的舒服还是去村里调研时候吃的农家菜,带着汤的烩面,面条煮出来的面汤……打个比较恶心的比喻,如果我是可以反刍的牛,我一定会品上那么几遭。吃喝这种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感受了——比如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农家饭,我就很喜欢。” 后来,谷教授真的逃离了北京,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广东教学生去了。广东我是不愿意去的,闷热的天气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广式美食在我的眼中只是偶尔打打牙祭用的珍馐异味。如果长时间待在广东是没有四川或者重庆的油辣子吃的,点心倒是精致,但最重要的汤又精致得有些过了,不够粗犷,不适合我这种土匪般端起碗牛饮的脾性。 喝汤的习惯我保留了很久:到东北馆子里吃饺子先讨完面汤来喝,吃完再喝一碗;在家里做饭哪怕是随便对付一点也一定会补上点什么汤去满足一下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甘肃的浆水,每次喝浆水总会有种异样的暖在挑逗我的神经,虽然从不曾有人为一碗浆水祈祷或是造作,但舌尖上不同于醋酸或是番茄的酸的刺激总能周济我因工作繁忙而略有颓废的精神。甚至在我去美国以后,哪怕是再人生地不熟也不得使我放弃这份念想。虽然味道甜酸油腻的美式中餐是我可以接受的餐点,但是因为缺了那一口热汤,我总会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好在加州人出了名的喜爱用猪骨和牛骨炖出来的汤浸泡着的越南粉,生活在圣何塞总是走不了几条街巷就能见到那么两三家生意还算可以的越南粉店,而我为了那一口十几美元的幸福感,总会搜罗着沿着街边的越南粉店,一家家品尝。每天和我一起觅食的家伙是个从小在中国长大而又喜欢日本文化的韩国王室后代,名叫李又平,我一般叫他“小王子”,我们总会在快要到晚饭点儿的时候相约去一起找点什么吃的。 前湾西智库联合创始人 自媒体人 硅谷码农 李又平(花名:小王子) 然而这座城市的夜晚总是不太平的,街上随处可见着精神错乱的疯人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疯人们嘴里叫嚷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或是逻辑,动作夸张的向他人问候或是辱骂,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得远一些;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大多是没有威胁的可怜人,多以老弱病残为主,每当我看到他们总会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但也有少数流浪汉长得魁梧壮实,在大街上朝我们这些抽着烟的行人讨要香烟。 “嘿,兄弟,我的名字叫迈克,没有工作且居无定所,请给我一支烟。” 带着一点点不情愿,我会把烟拿给他们。这个有时候说自己叫迈克又有时候说自己叫汤普森、约翰或是克里斯的家伙经常出没在圣何塞的downtown里面,是我见过比较多次的流浪汉。他接过香烟以后总是把烟嘴掐掉,然后用路人的打火机带着享受的表情把它点燃。我不希望流浪汉用手摸我心爱的带着家乡情感的中国打火机(我也不晓得我是如何把它们从北京带过来的),便总是替“迈克”们把烟点上,这时候他会堵住我,不让我离开,用饶舌歌的节奏讲述一个胡乱编造的背景故事,再向我讨要零钱。 “对不起,我一般出门只带信用卡,我的信用卡来自我的家乡中国,不可以提现。”说完,我会趁着他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而赶紧离开。这种寄居在城市里的流浪者总会把华人作为他们讨要钱财的对象,我原本还会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直到有一个说自己叫希尔的无家可归者骑着一辆崭新的、没有车锁的自行车出现在我面前讨要钱财的时候。 但即使是这样的夜,我和小王子也会出现在圣何塞的街头,偶尔我们会选择墨西哥的“布利多”或是“达科”,那是两种不同的卷饼,薄皮厚馅,新鲜筋道还带着汁水的牛肉碎粒配上大米和红豆的馅料形成了绝妙的组合,每咬下去充实的一口以后用手撕开还被包裹着部分的卷饼外面那层银色的锡纸,再在馅料上浇灌爽辣的白色蒜汁或是酱香红汁……如果说我最喜欢的快餐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些对味蕾有着绝妙刺激的卷饼了。然而快餐终究是快餐,如果硬要把快餐做成大餐就一定会像国内的墨西哥美食一样显得不伦不类。 还未卷好的“布利多” 很显然,快餐不能让我这个老饕有心理上的满足,现在回想起来,我比起“布利多”和“达科”更喜欢越南粉的原因多半就是这个了。越南粉分为很多种,每一家店做的味道都有些不一样。最常见的越南粉的汤里都会三三两两飘着几块儿零碎的洋葱,给我的感觉像是兰州牛肉面里面的萝卜,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来给汤调味儿的。棱柱形状的粉是煮熟了以后又在高汤里烫过才端上来的一大碗,细长而又筋道。虾仁、牛腩、排骨或是在汤里搁置不到三十秒就熟了的半生牛肉片供食客选择,选择到了适合自己的肉类就会产生快乐由得人选择的错觉。 其实越南粉也是很近似快餐的食物,属于餐饮工业化的产物,只是享用越南粉和在家里吃方便面是极其相近的,重要的是制造并体验它们的仪式感罢了。我喜欢干拌方便面的爽朗,不需要等待就可以大快朵颐的豪迈,但是泡熟的方便面却以仪式感取胜:这种仪式感包括用手撕开脱水蔬菜在内的更多调料包,把它们倾倒在热气腾腾的汤面里的流程,以及吃完方便面端起碗来往自己喉咙里灌冒着热气的调料汤的温暖。越南粉在上桌的同时还会附赠一盘需要加到汤里的配菜:豆芽、薄荷、青辣椒、待挤的半个柠檬以及一小撮九层塔(一种香料),就像吃过桥米线一样的把它们加到汤里烫熟。不同的是过桥米线的味道其实很一般,它不入味儿,但是越南粉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兰州牛肉面一样的,虽然佐以看上去颜色很清的汤却不缺味道。兰州牛肉面的豪放是手工拉扯出来的面条泡在浓郁的牛肉萝卜汤里,配上葱花、香菜以及醋和油辣椒以后的粗犷;而越南粉的温存则是隐隐在舌尖上和喉咙里停留的多种蔬菜和配料在被越南粉特有的高汤烫熟以后散发出来的性感清香,这种清香包含着酸、咸、甜、辣、鲜五种不同的感受,也包含着把每一种蔬菜用筷子拨到散发着热气的汤里、把柠檬汁挤出来时的走马灯式短暂回忆,这种舌尖上的感受对大脑的反馈就像接吻时感觉自己脑海中产生了电流一样奇妙,仿佛女儿家的矜持迈着优雅而又甜蜜的小步踱到口中。说到米线,我始终觉得炒米线要比煮米线好吃。而浓汤重料的小锅米线又要比华而不实的过桥米线好吃。但是炒米线难登大雅之堂,小锅米线在宴席上的竞争力也是远远不如过桥米线的,说到底还是人们对餐桌上的仪式感在作祟。如果西红柿和酸腌菜的酸味以最风情的比例结合到一起,韭菜和白菜丝的口感以最曼妙的吻合均匀在装着炒米线的盘子中,再随便配上一点什么汤就可以称得上是接近完美。如果可以选择这样一份朴实无华却又带着街头韵味儿的炒米线,我将会完全提不起对过桥米线的欲望。 在美国工作的台湾人Jove是我在美国生活的引路人,他曾经带我去离圣何塞有一段距离的的米尔皮塔斯吃整个硅谷最有名的“火车王越南粉”。那家店开在一个小广场中,突兀的小平房看上去简单而朴实,门口的食客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我站在队伍的末尾对Jove说:“嘿,这么多人挤在这么一家店门口,店老板岂不是要笑疯了。”Jove耸了耸肩,说:“越南人开的餐厅讲究的不是效率和服务,我们就先等着吧。”阳光很好,排队的食客们早就被硅谷的天气娇惯坏了,纷纷燥热的叉着腰摇摆身体,可我丝毫无法从他们的浮躁情绪中找到共鸣,我的心里只有对这一碗未曾谋面的“火车王越南粉”的期待。 落座,上菜。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摆在我眼前的冒着热气的碗着实惊到了我——那是一个比我在陕西关中见到的任何“海碗”还要庞大的“海碗”,碗里面飘着的除了晶莹白皙的粉还有来自牛身上不同部位的瘦肉以及一大块儿骨头。 火车王越南粉 Jove特别强调:“美国人不吃骨头上面的肉,他们认为啃骨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点了点头,一边用筷子搅拌着刚倒进汤里面的豆芽和柠檬一边说:“就像他们不吃带刺儿的鱼一样,放弃了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不带刺的烧鳕鱼美国人唯一可以接受的中式做法的鱼 那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吃到并非自己做的饭菜也并非典型美式快餐的餐食,越南粉的性感味道和豪迈的餐具形成了刺激我食欲的鲜明反差。当碗里的汤被我喝的一干二净以后,我问Jove:“如果我回圣何塞之后想吃这样一份霸道的越南粉,要去什么地方找呢?” “难点儿,”Jove想了想,“几年前我在你住处附近吃过一家,哪一家还挺不错的。碗没有这么大,但是用料特别足。那家店和今天你吃的这家店一样,是一栋小平房,开在一处平地上,店旁边都是楼房。门口有一圈栅栏,红色的房顶上是这家店名的英文和越南语版,我已经忘了店的名字叫什么了……” 因为Jove也早已记不得这家店的具体位置,我也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倒是越南粉成了我在美国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住处附近的越南餐厅都被我和小王子摸了个遍,直到有一天小王子说“老高,越南粉这种东西我都快吃腻了”,我才想起来这茬儿,于是和小王子一起按图索骥,胡乱想象着店铺样子在圣何塞的街头像瞎猫碰死耗子一样寻找传言中最好吃的越南粉。“在栅栏里有着红色房顶的小平房”是我们得到的对这一家餐厅唯一的有效讯息。终于在一条安静的街上找到一家看上去和Jove描述的场景有些相近的越南粉店。 “高老板,这里和你说的地方看起来很像。”小王子咗了一口他手里的“美国精神”,拉住正一边处理手机上消息一边前行的我。小王子原本是不抽烟的,这没事儿就来上两口的小嗜好也得益于我的荼毒。我把手里的炫赫门扔到地上踩灭,对小王子说:“走,咱们进去看看吧。” 店里的装潢很普通,和能在美国街头看到的一般餐厅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当我和小王子坐在桌子前拿起菜单来审视之时,我感觉我可能发现了新大陆:这家店把越南粉的汤底分为很多种,菜品的名目也是令人目不暇接。我面对这样一份菜单有些无从下手,便让服务员小妹给我点了他们家的招牌。不知是不是在美国生活的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向服务员解释清楚我需要的只是最受食客欢迎的那一碗粉。我等待了约摸一刻钟的时间,服务员端来一个底下垫着石垫的漆黑石锅,这种石锅我从未在越南餐馆里见过,它在我的记忆力只属于韩国的石锅拌饭,我的记忆一下子仿佛回到了我久居过的望京街道:那里是韩国人扎堆的地方,甚至在望京街头比较显目的韩文就像圣何塞街头的汉字一样随处可见。看着被服务员抬着的石锅,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韩国超市结账处摆着不同馅料的三角饭团,韩国烧烤架上吊着的新奇烟囱,还有帅气的韩国小伙以及漂亮的韩国姑娘……我不知道小王子对于他的故土是不是有这样一份视觉上的情怀,但是我在那一瞬间仿佛已经忘记了我正身处一家越南餐馆。这一切只是发生在这一个瞬间的事,当漆黑石锅被摆在我眼前,我立刻忘记了所有和这碗粉不相关的回忆,把视觉和嗅觉完全的交给了这碗粉。石锅里的汤黑里透黄,“滋滋”冒着带温度的泡儿,可以看出这间店的大厨应该放了不少油,目的就是给这碗粉提味。粉促狭地藏在汤里,只露出被一小撮香菜和饱满的豆芽遮盖着的冰山一角。汤汁一点也不似寻常越南粉的清爽,入口以后更是让我止不住粗鲁的大快朵颐,没有任何“性感”或者“曼妙”可言。我只是一刻不停地用筷子把热气腾腾的粉胡乱塞到嘴里,就算是已经被炖至熟烂的带筋牛腩和软糯中带着一丝香甜的胡萝卜也不能丝毫让我的动作减缓。随着碗中物不断地减少,我竟有些不舍得把快要见底的粉和碗中配物囫囵咽下去了。放下筷子,我感受到的不是无数个暴徒撬开我的味蕾,也不是胃里暖洋洋的润滑;我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夜晚不灭灯的公园和宽广空旷的大街,醉汉、疯人和流浪者似乎都和街边的一户户人家一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抬起碗喝下那一口浓厚而又饱满的热汤,我耳畔响起了这家店里食客们的餐具碰撞的声音,我也听到了城市里汽车鸣笛的声音和Bart(轻轨列车)一下下敲打铁道发出的叮当声。我突然明白:就像最好吃的煮米线是浓汤重料的小锅米线而不是什么“状元过桥米线”一样,最好吃的越南粉也并非是什么“火车王越南粉”。这家店绝对不是Jove描述的食物味道近似于“火车王越南粉”的红顶小屋,但我却牢牢记住了这家名不见经传而又特立独行的越南餐馆。 让人欲罢不能的“石锅越南粉”,食用时要浇上蒜末和红色的辣椒油 我和小王子在回程的路上载歌载舞。返回住处的路很黑,和夜晚美国街头上常见的灯火通明有些显得格格不入,我看着路标指示牌问小王子:“你知道这第八街,是咱们这边有名的保研路吗?”小王子摇摇头,他反问我:“高老板,什么是保研路?” “保研路,就是可以让学生保研的路。”小王子瞪大了眼睛,似乎没有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点上一支烟,吐了个不成形的烟圈接着对他说:“一般在学校附近,治安比较差的路会被叫做保研路。保研路经常有作奸犯科的家伙出没,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晚上单独走这条路有可能会被以抢劫为生的黑哥哥强奸。不只是女孩子,男生走这条夜路也是有被劫财加爆菊的危险呢。” “我靠,那我们还是不要走这条路了。” “那有什么的,很多学生不得已在晚上走这条路的时候都会在口袋里揣个安全套,防止染上艾滋。不过,要知道你亲爱的高老板再怎么说也是练过自由搏击的人,对付一个小混混变态狂简直简单加轻松。”我盯着小王子的眼睛,用炫耀般的语气告诉他他可以安心。 “是啊,有高老板在呢。”小王子挠挠头,想了想,又说:“可是高老板,你怎么知道你遇到的小混混变态狂只有一个人独身行动?” 我无语。但即使是这样,我和小王子也还是在这一周除了小王子有晚课的那一天以外的每个晚上都揣着急切的心情和一盒套套跑去光顾这家离住处隔了一条第八街的越南餐馆。这周日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悠闲地拍着肚皮从第八街走回住处,在我们刚到达我和小王子所住的五楼,正准备回到各自的小窝时,小王子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新闻:一名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于五分钟前在第八街遭到枪击并受伤。小王子说:“高老板,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条街吗?” 我对他回以一个美式耸肩,我说:“我没有听到枪声啊。” 从这以后,我和小王子心照不宣的谁也没有提过这家深烙在脑海里的越南餐馆,记忆中汤汁油光闪闪且冒着热气的汤汁和浓香扑鼻的特别味道也随着再不见这一碗越南粉而被封存了起来。 虽然我和小王子都不再晚饭时间结伴为觅食而穿过幽暗的第八街,但好在硅谷的饮食习惯还算是丰富,我可以不用走太远就吃到贴在铁炉子上烧熟的配上浓稠的鸡胸肉咖喱汁的印度风味馅饼,也可以坐在城中心的落地时钟旁边吃上一份不太正宗却又软糯迷人的海南鸡饭。小王子则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每天把自己浸泡在学校的DC(食堂)里。说来也有趣,我得以结识小王子这个家伙也是因为他带我去寻找DC。刚到学校的时候,我人生地不熟,见沙发上突兀的坐着一个长得像韩国人的家伙,便用英语向他询问:“不好意思,你知道DC在哪里吗?” 这家伙没告诉我DC在哪里,他说:“你要去DC吃饭吗?走嘛,我带你去好了。”他的英语很标准,没有近似亚洲人的口音,加上我的英语只能说得上是一般般,便没有和他聊天。从那一天起,我一直用蹩脚的英语和他交流,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的国籍也是中国,而且从小在深圳长大。 一不小心得知真相的我和他说:“李又平,你大爷的,我想一巴掌抽死你。” 小王子是个很随便的人,尤其是在吃这桩大事上,对他来说,每天吃DC里千篇一律的饭食并不是一件难事儿。我自认为我的嘴不是很刁,但如果只能选择一顿又一顿的美式食堂快餐,配上大锅煮出来的浓郁而又不适口的汤,我宁愿饿死。薯条是好东西,西兰花也是好东西,蔬菜沙拉也不错,但是我想,无论是哪一个对生活稍有追求的人都不能接受日复一日的面对着这些食物吧。我从来没有放弃对美食的寻找,即使幽暗的第八街已经在我这里成为了过去式我也依旧没有放弃——只是我想寻找的不单单是食物的给人的味觉,我要寻找的那种感觉看不见又摸不着,以至于我着实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一个天上下着紧密的小雨的下午,因为没有吃午饭而饥肠辘辘的我在街头寻找能够让我果腹又看上去还算不错的餐馆。原本一直“啪嗒啪嗒”的雨滴突然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全都变得急躁起来,前呼后拥着降临到柏油马路和人行横道上。我没有带伞,于是就近推开一家餐馆的门,落座,随手抓起桌子上的菜单来看。餐厅的名字很随意,叫“BoTown”,中文名叫“波城海鲜酒家”。侍者是两个广东老太太,考虑到我的粤语比英语讲得还要烂,我试图用普通话和她们交流:“不好意思,您家这个时间有什么配饭的套餐可以点吗?” “有的啊。”还好,普通话在这里用得上。“点饭可以送小吃和汤啊。” “都有些什么小吃?”我问。 “蟹饺啊、虾片啊,都有的。” 这个“都有”只是说有蟹饺和虾片两种选择,在美国的华人餐馆里,侍者建议的套餐内选择永远就是全部。生活在美国的人理解的蟹饺是一种油炸面食,里面的馅料就像生淀粉的口感一样奇怪。我要了一盘虾片,一份蒙古牛肉饭以及下午特供例汤。虾片上来得很快,我本来并不喜欢吃这种略带油腻的小食,但这阴雨连绵的一天似乎让我的口味有些转变。 虾片与酸辣汤 用手捏着吃了几片虾片以后,主食和汤都被女侍者摆到了桌子上,一共是两个菜,一荤一素。荤菜叫“蒙古牛肉”,拍过嫩肉粉的牛瘦肉片和洋葱炒在一起,底下垫着一层油炸出来的粉丝用作装饰;素菜是咸鱼茄子煲,泛着油光,在煲锅响着“滋滋”的声音,很是诱人。我拿纸巾胡乱擦了擦手,夹了一大筷子蒙古牛肉到盛了米饭的小碗里,酱油色的汤汁很快就渗到米饭的表层里去。我已经饥肠辘辘,便用筷子急切地把碗中物扒拉到自己的嘴里,虽然是狼吞虎咽,但牛肉裹上嫩肉粉以后肥而不腻的顺滑和大火炒至没有辛辣感觉的洋葱在嘴里和米饭一起越来越碎以及汁在嘴里水搅拌均匀的感觉是让我十分满足的。虽然不知道蒙古牛肉究竟“蒙古”在哪里,但是我还是在心里默默给了它一个好评。咸鱼茄子煲也没有让我失望,看来定居美国的老一辈广东人还没有落下手艺。这茄子烧得恰到好处,生抽、耗油均匀的和植物油一道铺在茄子的表面,佐以口味略有些咸过分的咸鱼,下饭极了。我只用不到一支烟的功夫就把眼前的美食一扫而光,然后端起那一碗不知是何方风味的酸辣汤仰着头一饮而尽,舒爽!虽欠了一些难以言表的极致追求,但也稍微安抚了我雨天觅食的心。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小王子的电话。 “Hello,Youpingisspeaking.” “是我,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我发现一家不错的中餐,你要不要来尝尝?” “哪儿?我骑滑板过来。” 挂掉电话,我笑了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也成了老饕界的权威。不大一会儿,小王子头发湿漉漉的出现在了我的对座,颇有些文雅地用瓷勺一口一口喝他才点的酸辣汤。我揶揄他:“多大个人,就不能豪爽一点?”他腼腆一笑:“高老板,广东人的汤就是应该这样精细着喝啊。”“广东的汤哪有这酸辣汤烈?净是些小火慢炖,又甜又淡的货色,有什么好喝的?”小王子皱了皱眉头,也不说话,端起碗来略有迟疑地把这一碗酸辣汤灌了下去。很快地,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他的眉头舒展开了,露出了一个颇满意的笑容,说:“我头一次觉得,中餐这么好吃。” “嘿!你这个吃韩料长大的小朋友,怎么可能吃过真正的中餐?锡林浩特蒙古包里整块儿冒着肥油的羊背、兰州马子禄家的牛肉面、大连街头夜市里从大铁锅里盛出来的焖子还有杭州西湖边上的酥软醋鱼,你吃过哪种?” 见小王子没有吭声,两眼睁大着看我,我接着说到:“还有,陕西不放青椒的肥而不腻的肉夹馍、绥中新鲜的八爪鱼捞上来炖的红烧肉……”,说着我突然停止了言语,我感觉还有那么多想要说得话没有说出来,喉咙里像噎着了似的。我听到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他,我有多久没有在熟悉的简体中文环境里大快朵颐了?回忆是不值钱的,经历也不是拿来炫耀的资本。聊以慰藉的,不过是带着些许情分的热汤罢了,仅此而已。 注:摘自作者文匪正在筹备的新书《会叫的狗也会咬人》 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爱德丰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hihuaz.com/shsjt/512.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留学一年的花费知多少
- 下一篇文章: 这些蠢萌漫画一张就能把你治愈得不要不要的